一个老专家的十年塞上行
5月25日,天刚蒙蒙亮,70岁的梅占魁照例早起,他穿上大红的绸缎外套,用一顶鸭舌帽遮住因化疗而光亮的头,努力藏起病容,微笑着接受100多名宁煤同事自发为他筹办的生日宴。可宴会最后,他还是没止住泪水:“老天让我再多活两年就好,我还想……还想为宁煤做点我该做的事。”
一个月后,这位在戈壁滩躬耕了十年的老人,带着煤化工事业未竟的心愿,走了。
对这位返聘的技术顾问,宁煤人以正式工的身份安葬他。宁煤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姚敏说:“老爷子将生命的最后十年奉献给宁煤,为重大项目的设备吊装竭尽一生,贡献巨大,我们永远缅怀他。”
外聘顾问何以树起威信?
倔老头脾气大,本事也高
戈壁滩上的风,吹过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上矗立的座座高塔,簌簌作响。2002年,神华宁煤集团担纲宁夏“一号工程”——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排头兵,建设煤化工项目。这对于一直以挖煤为生的宁煤人来说,无疑是“摸着石头过河”。缺少相关领域的人才成为首个“拦路虎”。
时任甲醇项目筹建处工程部副部长的李晓东记得第一次见到梅占魁的样子:“他戴着一顶半旧的老头帽,拎着个破包,来给宁煤员工讲课。他当时是施工单位推荐的授课老师,刚从中国化工第六建设公司退休。”
短短几十分钟的课程,梅占魁讲了大型机组的安装,对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关键问题剖析透彻,原本已疲乏的宁煤员工纷纷向时任甲醇筹建处处长的姚敏建言:“这个老爷子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没想到从此以后,宁煤的甲醇项目、煤基烯烃项目、煤制油项目所用到的大件设备都贴上了梅式“标签”。“这些高塔都是在老爷子的手底下吊装起来的,没有梅总就没有今天的投产、运营。”如今已是煤制油项目副总指挥的李晓东眼含热泪。
“老爷子脾气大、有点倔,认定的事情从不妥协。”煤化工安装检修公司经理左新荣对梅占魁的第一印象可不太好。那天正值甲醇项目组开协调会,不少人对商定的方案热情高涨,没想到坐在旁边的梅占魁兜头一盆冷水:“你们简直是胡说,这么做,有很多潜在问题。”
这是梅占魁的一贯风格,也为他招来不少埋怨,但是不久之后左新荣却成了梅占魁的弟子。“事后来看,他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具有前瞻性,要不是老爷子在,我们会走很多弯路。”左新荣说。
在煤化工各个项目中,大件设备的制作、运输、吊装是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关系着后续生产的开展。梅占魁对于工期的“苛刻”经常让施工方和技术员们大呼“要了命了”。
施工方经理阚文忠谈起一段往事。甲醇项目筹建期间,为了吊一座常压精馏塔,梅占魁冒着雨雪在现场跟到晚上十一点多,阚文忠看不下去了,把他硬拽到车上送回家。“这是一个霸气的老头儿,定的工期说一不二,但也是个有本事的老头,对于工程有大局观,对吊装各个环节的摆布事后看来都是极有道理的。”
由于梅占魁的坚持,甲醇项目吊装比预期提前了四个多月完成,为集团公司节省了一大笔费用。原本对他有所抱怨的施工方也竖起了大拇指:“嘿,这老梅头真行!”
一有闲工夫,梅占魁就拉着阚文忠一起研究设计方案,这原本只是施工方的事,梅占魁却一字一段地看,提出修改建议。“他能站在我们施工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也不把自己当成外聘的,很多事敢于拍板,所以大伙儿都服他。”在梅老的生日宴上,阚文忠特意唱了一首《父亲》。
熟悉梅占魁的人,都叫他“老爷子”,经他手竖起的大型设备总重达到70000多吨。截至2011年底,梅占魁指挥吊装的6个煤化工项目,不仅生产出84万吨甲醇,更让世人瞩目的是,年产50万吨煤基烯烃项目,产出质量达到GB338-2004优等品标准的产品。
为啥年轻人争当他的弟子?
愿意倾囊相授的“技术大拿”
“手托腮,抠着牙,瞅着你笑。”梅占魁的关门弟子李晓东回忆起师傅的日常情态,特别是每遇项目难题,最难忘的就是这样的笑。
在宁煤十年间,梅占魁的弟子无数,真正拜了师的只有李晓东和左新荣两个。不少弟子都说梅占魁爱骂人,对工作要求极其严谨,经常唠叨“不严谨就别干技术员”。
梅占魁的“严谨”也让宁煤的年轻人看到了他的真本事,烯烃项目试车的时候用的是德国西门子的专利设备——气化炉,这也是该设备在世界上的首次工业化应用。让所有人都傻眼的是,气化炉在试车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难以满足生产要求,外国来的技术员也束手无策。
梅占魁二话没说,带着几名工程师干了起来,对不符合实际要求的部分进行改造、重装,没想到干成了,设备成功运转了。自此,宁煤集团对西门子的气化炉占有50%的利润分成。连公司的外国技术顾问盖瑞对此事也连连称服。
“一般的技术大拿,传授经验的时候都有所保留,老爷子不是,你问到的,只要他知道,都会告诉你。”煤制油项目控制部部长张自明说,他跟老爷子认识了十年,在许多重大项目上都有合作。
阚文忠和李晓东都记得,梅占魁办公室里有一张大方桌,被一张图纸铺满,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红绿绿的标注,哪个设备要运、吊车怎么走、通道留多少等,记得一清二楚。老爷子一手夹着笔,一手拿着放大镜仔细审看、修改。“被他骂是常态,但是到办公室里他都会对照图纸细心讲解,不记得骂过你。”李晓东笑道。
由于上班时间多在工地,吊装协调会一般在晚上七点以后开,通常开到晚上十一二点,几碗拉面、两道小菜是老爷子和徒弟们的加班餐。李晓东爆料师傅的一大爱好:饭桌上,梅占魁时不时用手指在某个人面前点一点,“来,我们研究下这个问题”。“不分时候、不分场合,只要他想到了,就会跟你说。”李晓东说。
年产25万吨的甲醇项目建成了,年产50万吨的煤制烯烃项目投产了,年产400万吨的煤制油项目开工了……这些具有全球性挑战的项目让原本寂寥荒凉的戈壁滩涌起了生产建设的滚滚热浪。然而,爱挑战的梅占魁总是不满足于现状。煤制油项目总指挥蔡力宏望着设备高塔,叹了一口气:“老爷子常跟弟子们说‘你们别太得意,难题还在后头呢’,这句话始终在鞭策着我们前进。”
十年间,梅占魁踩过基地的每寸粘土,“玩”过当时世界顶尖的1600吨吊车、4000吨吊车,吊起过被称为“世界性难题”100.3米高的C3分离塔、96米高的净化吸收塔,完成了数百件大型设备制作、安装,也带起了一批掌握先进吊装技术的宁煤人。
工作较真,为何其他别无所求?
肩上有责任 心中有痴爱
姚敏清晰记得2006年他去请梅占魁的场景,当时煤化工项目还在初创期,集团公司请来一批专家,梅占魁不像别的专家会问问年薪、待遇、住房,而是问来了能做什么事,集团的氛围环境和现有团队是怎么样的。“我从心里也更加认定他了。”姚敏说。
应梅占魁的要求,公司在离基地最近的居民区租了一套60平方米的住房。原甲醇筹建处办公室主任张有国负责梅占魁的起居安排,他记得梅占魁跟他说得最多的是“好着呢,小张,没有任何事”。
“这个老人太省事了!”张有国想不通,每逢开会、考察,公司配备大车和小车,但梅占魁总说:“我上大车,和大家挤一挤,热闹。”
“一切源于他对吊装的痴爱,以及宁煤和这片土地给予的平台,其他任何事情他都不关心,包括身体。”和梅占魁同在中国化工集团共过事的涂玉祥说。2014年10月,梅占魁被查出肺癌晚期,卧病在床期间,他变得嗜睡,可是每有同事来看望,谈及工程建设情况,他的眼睛就会睁大,也有了精神头。
阚文忠时常把基地情况拍下来传给梅占魁的小儿子,为的就是安慰鼓励老爷子养病。一次他接到梅占魁的电话,那头传来愉快的声音:“你小子,知道我想看什么。”那次通话,梅老又跟他讲了许多注意事项。
穿着四五斤重的劳保鞋,爬几十米高的框架,在工程项目现场的梅占魁全然不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一次吊装作业,梅占魁穿了一双单鞋站在雪地里,阚文忠有些心疼:“你老爷子咋这臭美呢,快回去换双棉鞋吧。”梅占魁只是笑笑。
和梅占魁相伴近五十年的徐华珍,随丈夫的工作调动辗转了很多地方。2007年她来到银川,照顾梅占魁的饮食起居:“一年365天,他在家的时间统共不过30天,他在任何一个工作过的地方待得时间都比家里长。”
梅占魁睡眠不好,通常一天只能睡四个多小时,半夜睡不着就在客厅看电视,必看的是天气预报,因为宁东风大,吊装易受影响。天不亮他就出门,到了基地,司机总想多拉他一会儿,但是老爷子将手一摆道:“你拉着我,我怎么看设备,怎么知道哪里出问题。”
去年11月,从北京住院回来的第二天,梅占魁提出想去现场看一看,谁劝都不听。从车间到厂外现场,原本十来分钟的路程,他走了一个多小时。
躺在病床上的几个月里,梅占魁没说过几句话,后来癌细胞转移到大脑,他彻底失声了。徐华珍记得他说的最多的是,“如果可以再活两年,就能看到煤制油项目的建成了,心愿也就了了”。
记者手记
爱了一辈子 干了一辈子 值了一辈子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放弃在北京颐养天年,来到寂寥荒凉的戈壁滩,在风吹日晒的基地现场,一干就是十年?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群人的身上找到答案:像候鸟一样追赶太阳南来北往育种的袁隆平、夜间义务挂箱上门服务的技师徐虎、24小时随叫随到的医生贾立群……他们对事业无比热爱,一辈子专心付出。
梅占魁总说自己还有未了的心结--没有看到年产400万吨的煤制油项目建成,答应姚敏要写一本吊装技术的书,没有写。可是,临终前他也说过,人活百岁怎么样,活了六十岁又怎样,只要做了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就很伟大,他不亏,值!
翻开梅占魁的履历,会发现他将近五十年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层一线度过,从技术组长到施工主任、总工程师,再到宁煤集团的技术顾问、攻坚组组长等,他吃住在现场,带领技术员和工人不离现场,指挥大件吊装、开展技术攻关全在现场,卧病期间,他在病床上看图纸,用手机了解现场情况。
有句名言:激情是做好一件事的素养,这句话用在梅占魁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他将自己的深爱的事业做到极致,爬到了巅峰,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风景。
不是神人,不是能人,是对工作绝对严谨认真的人,梅占魁的老伴徐华珍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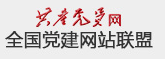




 湘公网安备 43042302600018
湘公网安备 43042302600018